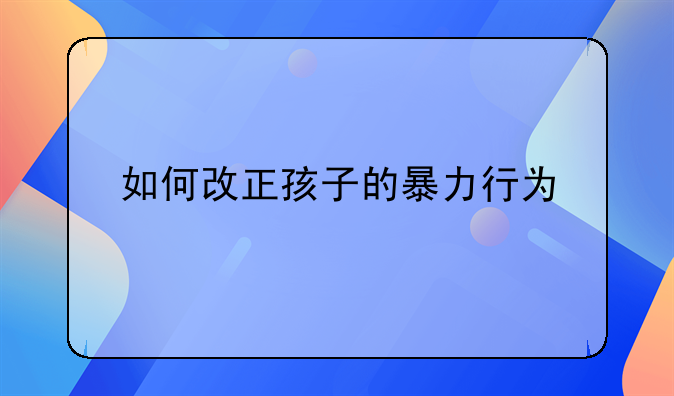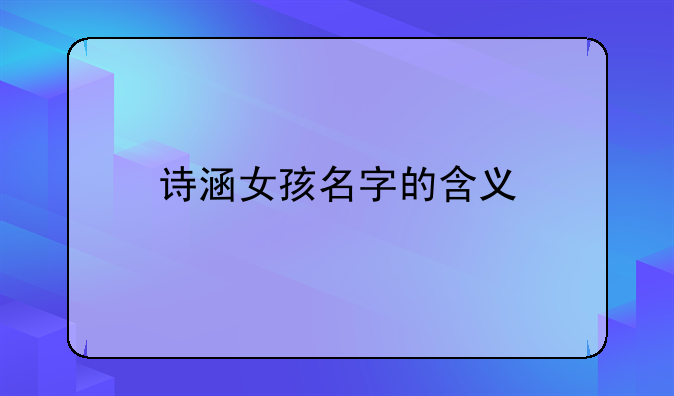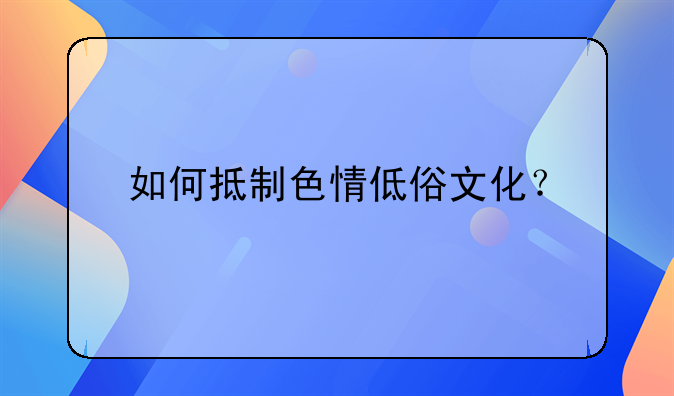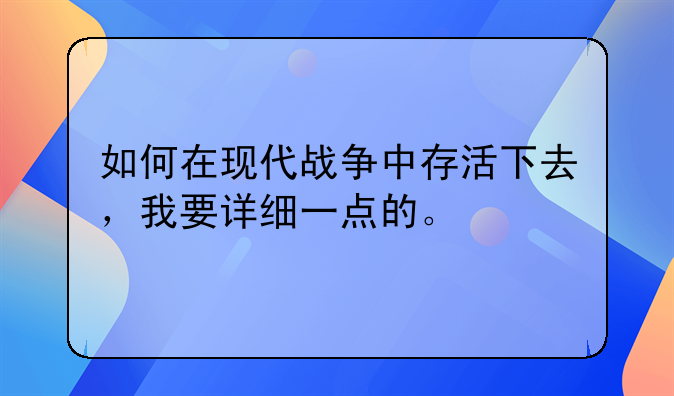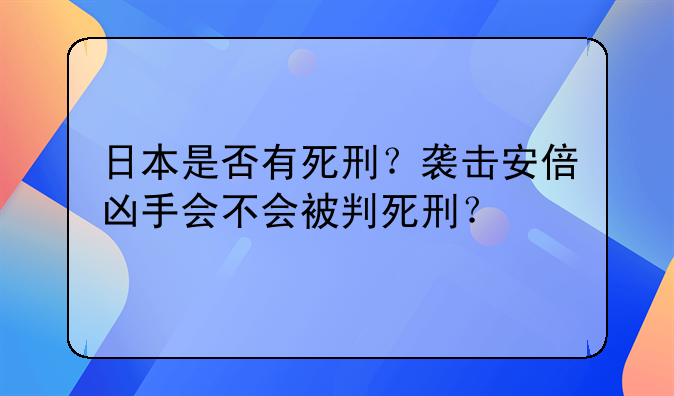暴力美学神作——暴力美学讲的什么
- 1、聊聊|电影中的暴力美学,来细品它的极尽高级
- 2、如何看待性暴力美学这一概念的流行?
- 3、什么是暴力美学,为什么暴力也是美学的范畴
本文提供以下相关文章,点击可跳转详情内容,欢迎阅读!
聊聊|电影中的暴力美学,来细品它的极尽高级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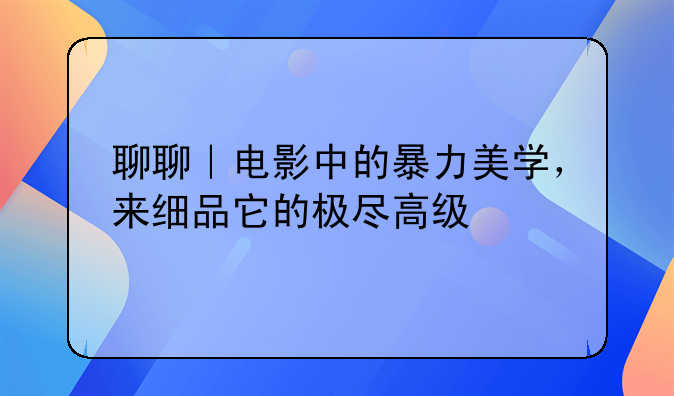
答说到暴力美学,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暴力美学教父昆汀的一系列神作
《
杀死比尔》
,
《被解救的姜戈》
这些经典代表作。并且由于《杀死比尔》主演刘玉玲在《致命女人》中的超A气质,她早年在《杀死比尔》中的日式和服配以武士刀的镜头又再一次登上热搜,散发着冷冽且独一无二的东方美感。
这是带有纯粹的高级美感的,所以这叫经典。
然而似乎是,暴力电影总是与
“
飒”,“无情”,“酷” 等词汇挂钩,但这样的标签,又与犯罪动作电影有什么直接区别呢,所以我觉得,暴力美学的界限一直都不够明确,极易混淆。
近些年被称为暴力美学的爆米花电影,有以小丑女的性感出名的
《自杀小队》
,有女主凭不可能的运气活下来的
《准备好了没》
,都是质量偏低,节奏感较强的爆米花电影,且人物刻画缺乏细节,剧情走向缺乏逻辑,属于一种短时间的“热度”电影。
这种为了暴力而暴力,为了血腥而血腥的设定,算不上美学,也就最多归属一个暴力吧。
想要达到一个美学的level,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元素,就是
“情感”
。
暴力,一般指一种故意伤害的心理,其源头便是旧社会的人们,在强压下所以产生的一种
对抗行为
。所以我会说,暴力是基于一定的情感酝酿在里面,不可能像一般套路一样, 都是没来由的精神病患者。
1 9 8 1. 5. 2 5 戛 纳 电 影 节
其实很多人看这部电影,其实更多可以称之为,这一场
“行为艺术”
的表演,是因为女主角阿佳妮的颜值,我也不例外。然而阿佳妮的照片,很多人用来做头像,用来做聊天背景,甚至一度成为非主流的潮流群体之一,这一点,并不太妙。
不过插一句嘴,像她这样有颜值有演技的,放在现在,真是屈指可数,不过这要是细讲就是另一堆事了。
回到正题,这部电影,很多人讲可怕,其实我觉得,观影过程中,血腥污秽场面,还是很牵引注意力的,表达的非常直白,可能会被某一镜头恶心到,比如为电影史留下的经典一幕:女主角与恶魔的交配。
以及女主在地下通道中,浑身战栗抽搐的过渡反应。一边进行着自我的内心斗争,一边进行着身体与灵魂的融合,因为刺激反应而留下的液体,都使女主更加完全的向恶魔转化。这一段的表演,在恐怖片历史中确实有这一席地位,其冷色调和扭曲感又融洽又给人一种颠覆情感。
只能说确实有不适感,但我更震惊于导演的处理方式,以对于人体的虐待式的方式,来展现人物内心变化和其强烈程度,这样的手法是非常有刺激性的,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刺激性,更加直观的在展示着一些“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包括对于血腥感的描绘,整部影片都充斥着一种摄影和配色上的美感:一种冷色调中的鲜红点缀。
不过至于恐惧,我觉得更多的是后怕。
1 9 8 0. 5. 2 3 美国
这部电影和《着魔》的最大区别就是,极少血腥状态。靠着人物的行为,最主要是表情,展现内心斗争。而其成功之处也是面孔上的拿捏,而映射出的一种恐怖。
比如女主角的长相,诡异,棱角分明,双眼异于常人的大。
在惊悚电影中,这一类的长相其实是很难得并且时常被青睐的,就比如蒂姆伯顿的《僵尸新娘》的长相也是异曲同工。
其实影片中最可怕的地方,并非海报上那经典一幕。
所有对情绪的铺垫,这个酒店给人的心理暗示,都是给人留下了细思极恐的空间。
不断重复的打字机
是酒店主人的鬼魂还是男主角的臆想?
男孩骑车的第一视角
已经死去的双胞胎为何会与小男孩相见?
酒店神秘照片
这是酒店主人的阴谋还是男主角内心的空虚映射?
很想知道,闪灵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诅咒。
2 0 0 6. 5. 2 7 日本
整体基调与上两部非常不同,这部电影走着一种黑色幽默喜剧的风格,要说近期热播的《我是余欢水》,就有着一种相似的讽刺意味。
这一部电影的暴力之处,在于扎心。
通过一些暴力的表现形式(松子被歧视,家暴的一些肉体冲突,以及松子外形的变化),来表现松子的“惨”,来让观影者深刻去体会:“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松子”。
高级美感之处,除了日本电影特有的饱和色调,还有就是对于场景的刻画。
随着剧情的深入,观影者更加沉浸在对于松子悲剧人生的哀悼中,这个时候,鲜艳而丰满的色调,与之形成浓浓的对比,悲剧色彩仿佛更加强烈了。
最为暴力的地方,是压抑。
为了取悦父亲而做鬼脸,松子的内心是悲凉的。
做了第三者的松子,终究被抛弃。
为了利益而杀人,松子是在发泄吧。
因为想要爱而去黑社会做情妇,松子的人生已经坠入深渊。
是这个世界负了她,还是她过于信任这个世界。
最后落寞的自己,却有着满天繁星。
生而为人,对不起。
松子和太宰治仿佛两个平行世界的人,发生着相似的,被这个世界所折磨的遭遇。
暴力美学,不是什么很“爽”的事情,而是通过一个个暴力血腥的场面,去描绘一颗颗被压抑的心。
撰文:心肌女一号/田孟禾
排版:田孟禾
合作邮箱:u571yq259@163.com
如何看待性暴力美学这一概念的流行? (二)
答你好呀亲亲,我认为性暴力元素在电影中并不罕见,观点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在许多电影中,这种元素的植入是别有用心、令人反感的:无论是在像詹妮弗·劳伦斯主演的《红雀》这样的主流惊悚片,还是在像《人间,空间,时间和人》这样的艺术电影中都是如此。主要由以下几点褒贬不一来侧面分析性暴力美学在影片中的含义:
1、虽然男性能够利用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吸引女性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而还是会通过各种强硬手段故意去占女性的便宜。这显然与生理需求无关,而是一种对控制欲的满足;侵犯女性的男人并不是什么只会在惊悚电影里看到的怪物,而只是想要拥有权力和控制女性的人。
2、有的电影会以象征主义的拍摄手法为由,对事件的结果避而不谈,因此,电影中的强奸情节很多都是为某个更繁复的问题作了垫脚石,对于受害人的实际伤害则甚少提及。《猎凶风河谷》、《夜行动物》和《一个国家的诞生》这三部风格迥异的影片都讲述了女性受害者和她身边的男性的故事。但故事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女性遭受的肉体侵犯上,而是只着墨于男性角色自尊受到的伤害,和父权制秩序的暂时破坏等问题。
3、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意识地去抵制性骚扰现象自然是好事,但我希望人们也能多多关注电影中的性暴力元素。电影不应只表现强奸行为本身,还应探讨受害人所受到的心理创伤。
4、为了提高人们对性侵犯问题的持续关注度,电影中的性暴力元素不能再成为剧情发展的垫脚石,受害者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也不能再被一笔带过。我们只能希望会能有越来越多的电影——无论是商业影片、独立影片,还是艺术影片——能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关注性侵犯问题的真实现状。
总而言之,我更希望第四点,性暴力能让社会各界对性侵犯问题加以关注,而不是作为流量来吸引眼球。亲的问题
什么是暴力美学,为什么暴力也是美学的范畴 (三)
答“暴力美学一词的由来,有待考证,但作为一种电影艺术的风格和表现手法,却是 实实在在的存在。 它是以美学的方式,诗意的画面,甚至幻想中的镜头来表现人
性暴力面和暴力行为。观赏者本身往往惊叹于艺术化的表现形式,无法对内容产生 任何的不适。支持人士往往称“暴力程度与票房收入成正比”,社会道德捍卫者和
舆论谴责人士则称其是对社会道德教化的阻碍和负面影响。” 昆汀·塔伦蒂诺的《KILL BILL》是这两年暴力美学的典型代表,你“拿斧子 削尖脑袋挤进江湖”这么血淋淋的事情是暴力,但又是有美学倾向和美学目的,所以说是暴力美学。
在讨论昆汀·塔伦蒂诺的作品时,被使用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暴力美学"。还有的介绍文章居然将"暴力美学创始人"的头衔戴到昆廷这个电影界的"坏孩子"头上。其实,就美国电影而论,以下几部作品可以用来描述暴力美学发展的轨迹: 1967年由阿瑟·佩恩导演的《邦尼和克莱德》,1969年萨姆·佩金·帕导演的《野蛮的一伙》,1971年由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发条橘子》,1976年由马丁·斯科西思导演的《出租车司机》,等等。但是如果论及对"坏孩子"昆廷的影响,如果论及暴力美学作为一种具有电影史意义的风格形态的成型和完全发展,则应将焦点聚集到香港的电影人和创作。
吴宇森、林岭东是昆汀十分熟悉并且经常挂在嘴边的导演。昆汀作品中有的暴力细节则直接来自香港影片。近年来所谓"暴力美学"是有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的,它就是指在中国的香港发展成熟的一种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它发掘出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中的形式感,将其中的形式美感发扬到眩目的程度,忽视或弱化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但是就改变现实形态和营造强化的视觉、听觉形象来说,其美学思想和技法的远祖却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爱森斯坦。
爱森斯坦1923年在《左翼文艺战线》上提出"杂耍蒙太奇"(近年被准确地译作"吸引力蒙太奇")的理念。他把电影视为表达主题思想和阶级观点的手段,而且他说电影只能用于这种"宣传、鼓动"。"杂耍蒙太奇"明确地表现出一种哲学和历史判断的教条式绝对自信,并导致作者在认识论上的过于强横的权威性。对于观众来说,它则造成艺术观赏与现实关系的封闭――因为由社会生活到思考认识的过程已经在电影导演那里完美地、一次性地完成了,观众到电影院只是去接受结论、聍听教诲而已。这种历史判断的绝对自信要求一种话语上的强权。爱森斯坦有些彻底贯彻杂耍蒙太奇观念的电影作品,不是试图在交流、循环中让观众认同,而是耳提面命,把作者的思想像楔子一样敲进我们的脑中。――的确,如何在冗杂的生活中引出作者的理解并尽量让观众接受,是今天的创作者仍然要面对的难题。但是,要像爱森斯坦这样使用杂耍方法就太简单了。在本质上,杂耍理念其实通向一种不可知论。因为那种封闭而绝对自说自话的电影语汇使观众感到只有作者"真理在手";对于观看影片的人来说,认识已经完成了,结论已经有了,观众在电影作品面前完全是一个接受灌输的思想容器。换句话说,在爱森斯坦的电影院里,观众完全是一个"自在之物"。
爱森斯坦哲学和历史观的绝对自信,使他在美学上有一种过分的野心――他觉得他可以绝对控制观众的反应。他把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引入了电影,认为可以在美学上实现条件反射式的意识生产。作为一个形式理论家,爱森斯坦进一步主张:意识是一套形式进程,可以在感觉、情感、认知三个阶段中统合个别的生理反应。他假设意识包括感觉、情感和认知,三者只有物质等级上的差别。"人受到基本的节拍蒙太奇的影响而动摇,跟受到其中心智进程的影响而动摇是没有根本差异的。因为,心智进程原是同样的骚动,只不过发生在比较高级等级的神经中枢领域中。"1)
这是美学上的乌托邦理想,它是和政治上的极端功利主义紧密结合的――即试图找到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生产机制,以便批量化地生产具有阶级觉悟的群众。这完全是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信念,这种思想超人并不打算与观众讨论、交流作品的思想和观念,而是用直接的概念和物象连接来说出"主题"。这其实是一种美学的暴力。
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作者的倾向也应该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流露出来"。对于那种使人物成为作者思想传声筒的创作方法,马克思称之为席勒化。而杂耍蒙太奇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强化的、直白的,作者经常明确地跳出来说出主题。
在艺术和现实的关系上,作者经常混淆记录和加工的界限。这就封闭了观众二次读解的途径,封锁了读者自己阐释文本和认识社会的途径。例如,爱森斯坦的《墨西哥万岁》就是一部说不清是故事片还是记录片的电影。作者把记录性素材和搬演的场景、动作剪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虚构的却以"纪实"形态出现的情节影片。这就是美学上十分暴力的方法。这种影片不像今天的《科学探索》这类影片,那里面的事后扮演是明确告诉我们的;而且在这种介绍知识的影片中,它的记录没有本体论上的意义。
我认为,当杂耍的意念过于强烈、过于急功近利地表达作者态度时,会在美学上给人一种暴力感觉。例如,爱森斯坦的学生米·罗姆拍摄的《普通的法西斯》在很多电影学校是作为记录片来讲的。他在这部影片当中有意识地贯彻了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的观念。有些地方的杂耍蒙太奇手法也确实造成了比较强烈的对比和视觉冲击力。但是,我认为这部影片虽然有明确的反法西斯意图,在美学上却有十分强横的意味。它在美学上重新走向了暴力,而"美学的暴力"正是法西斯美学的特征之一。
暴力美学恰恰是对吸引力蒙太奇(杂耍蒙太奇)的艺术技巧的清洗和拯救,对于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原意却是一种背离和异化。暴力美学当然受到美国电影的启发,但就其摒弃表面的社会评判和道德劝戒而言,就其浪漫化、诗意的武打、动作的极度夸张走向彻底的形式主义而言,却是在香港完成的。在它成熟以后又反过来波及美国,经过昆廷的发扬又启发了奥里佛·斯通等人的一些影片。《英雄本色》、《低俗小说》、《杀手雷昂》、《变脸》、《天生杀人狂》、《骇客帝国》等影片都是暴力美学的代表性作品。这一"时髦"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华人导演李安。
在我看来,暴力美学表面上弱化或者摒弃了社会劝戒或道德审判,但就电影社会学和心理学来说,其实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是对杂耍蒙太奇观念的彻底反驳。它意味着电影不再提供社会楷模和道德指南,电影也不承担对观众的教化责任,电影只提供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当然,它所面对的,也是产生它所必不可少的社会环境是:具备商业伦理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观众,后现代社会,高度法制化社会,有自由竞争的文化空间,有自由的文化产品选择权。
细致分析起来会发现:"坏孩子"昆廷更偏爱一种暴力情景以及残酷的情节和意象,不像香港电影人那样发挥暴力的诗化魅力,将暴力虚化为一种唯美主义的镜语表演。如果说香港的暴力美学更多浪漫和温情的色彩,那么昆廷的暴力展示则更富于黑色感觉和犬儒主义的笑脸。――顺便说一句:在一个高度商业化、法制化的社会,这种不管不顾、无忧无虑的犬儒主义顶多算是一个"无害的坏孩子"的"无害的冷漠"而已,是自由的审美态度之一种。但是,在真正黑暗、荒诞的境遇中,那些看一切都正常,到哪里都觉得莺歌燕舞、阳光明媚、如鱼得水的人,也极可能对人和生活持犬儒主义观点。因为他觉得一切本来就是如此,一切也就应该如此,这种犬儒主义的冷漠在我看来却十分可疑。
在剧作和情景上,昆廷更喜欢一种无铺垫、突如其来的杀戮或死亡。看看《低俗小说》中那个拿无头尸体和汽车后座上的血和脑浆来说事、搞笑的段落也许会让我们后背冒出些许凉气。
昆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也许,昆廷与奥利佛·斯通在《天生杀手》的合作及矛盾,可以反映出他与坚持现实思考和社会评判的导演的差异。昆廷说:"在《天生杀人狂》中,你不会看到我的影子,因为奥利佛·斯通的声音完全盖过了我,而大家亦会视《天生杀人狂》为他的作品。"《天生杀人狂》拍摄时已有传闻说二人闹翻,因为奥利佛·斯通把坏孩子的剧本改得面目全非,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昆廷的名字写在"故事"一栏。
昆廷曾经认真解释:"我不憎恨史东,但我为此事不高兴。我和他的风格和触觉全不一样:他喜欢将失望呈现开来;我则由得那些事情发生得无缘无故。他当然不赞成这种做法。我简直想象得到,如果斯通向一千人放映自己的戏,而那一千人不完全掌握他的意思,他会认为自己很失败。我最欣赏他的冲动,但他那种不言而喻的表现方法确是浪费了他的精力。"2)昆廷说自己曾经与奥利佛·斯通这样对话:"我曾问他:'你是个好导演,为何不拍一些平易近人的戏?'其实我是问他为何不拍像《水库的狗》一般的戏。他说:'我就是以这态度拍《天生杀人狂》。'我当然说《天生杀人狂》野心很大,甚至比他过往的戏更大,好似拍着一部'奥利佛·斯通漫谈美国暴力与连环杀手'。奥利佛·斯通教导似地对我说:'《水库的狗》只是一部戏(movie),要知道你是拍戏,我是拍电影(film),马丁·斯科西思、吴宇森都是拍戏。十五年后你看回自己的戏就发觉我说的不错。'他说得很对,我不想拍'电影',我喜欢拍戏。"
"他还跟我说:'你才二十多岁,你拍的是有关戏的戏,我拍的则是我四十年的人生阅历。我见过的暴力比你多,我到过越南打仗,中过枪。你真的想谈暴力吗?好,那就实实在在地谈吧!'"3)
老前辈的话果然说中了几分。昆廷最严重的暴力经验,顶多是在学校打架,还有十多岁时在店铺偷了一盒录影带。我的看法是:奥利佛·斯通比昆廷对暴力有更深切的体会。昆廷可能不会想到,要真想玩弄暴力美学,首先要身体安全。昆廷就是有点"少年不知暴力滋味"。此外,昆廷也不会想到,话语表演是要有社会保障的,一旦没有这种保障,话语表演就意味着流血。这使我想起1968年前后,福柯在法国大谈文化大革命和什么民众正义(就是我们文革中实行的群众专政)的情景。其实,福柯对话语游戏、语言反叛和行动暴力会得到什么还是心中有底的。从这一点,我看到他与政治体制之间还是有一种信任关系。那时他"身着笔挺的西装,和学生们一起从屋顶上向楼下维持秩序的警察扔砖头,开心得很。他之所以能够开心,多半以他的人身安全并没有受到丝毫威胁为前提。当时他在巴黎郊外一所大学任哲学系主任,系里开设'文化大革命'、'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之类的专题课,向戴高乐政权挑战。人们尽可以说法国社会对人权和理想的尊重是虚伪的,但是言论自由毕竟受到法律的保护,教授们决不会像张志新那样因为敢于直言而被割断声带。就因为人权有基本保障,他们才可以言所欲言,不必有任何顾忌。"4)而这一切,昆廷是没有兴趣关心的,大概他更关心在这个保障健全的社会里如何玩得开心,玩得离谱,玩得让整个世界都来惊诧和叹服这位"坏孩子"的天才。
人天天都会学到一点东西,往往所学到的是发现昨日学到的是错的。从上文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暴力美学神作。如需更深入了解,可以看看酷斯法的其他内容。

 家庭婚姻
家庭婚姻 刑事辩护
刑事辩护 债权债务
债权债务 公司法
公司法 房产纠纷
房产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 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 医疗纠纷
医疗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