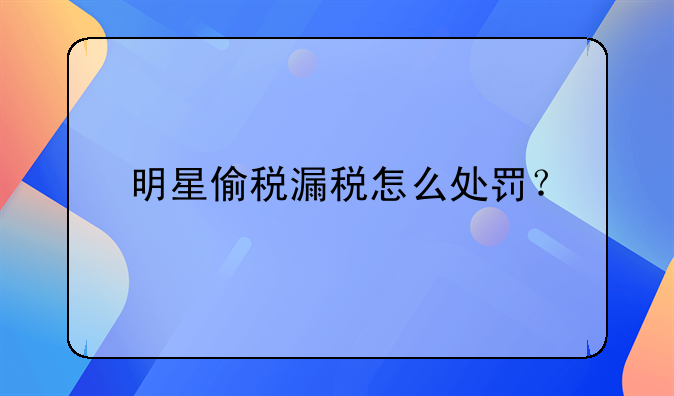上海市诈骗罪量刑标准2020年-2021年上海诈骗量刑
【导读】
刘律发现,在个人在进行交易虚拟币的时候,存在着这么一种违法犯罪情形——犯罪分子谎称要购买虚拟币,线上联系好虚拟币卖家后,带着现金,线下交易。交易过程中呢,等对方把虚拟币转到犯罪分子钱包后,犯罪分子一口咬定说没有收到,然后转身就跑!这种“空手套白狼”型的虚拟币诈骗案,实务中还不止一起案例!接下来,刘律就带大家看看,这种诈骗虚拟币的模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案情引入
最近,在广东省惠州市【(2023)粤13刑终398号】李某亮、张某等合同诈骗案,就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型的虚拟币诈骗案!
案情是这样的:李某亮一伙在网上结识了想要出售USDT的被害人王某。于是,李某亮等人向王某谎称有意购买USDT,并与王某协商好了交易的USDT数量和价格,约定通过线下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交易。
交易当天,同案犯张某携带了一个装有现金的双肩包前往交易地点。这个包里,只有最上面的一层是真实的钞票,下面则用尿不湿来填充,制造出一包现金的假象。张某的任务是用这个包来骗取王某的信任,让他相信李某亮一伙交易的诚意。
看到这里,有人肯定就要问了:法治社会!碰上这种诈骗虚拟货币的事,在对方明明已经收到币却又矢口否认的时候,为什么不报警?最近呢,刘律正好接到了一个这种类型的虚拟币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在口供中直言不讳地说:我此前也被别人通过这种方式诈骗过价值几百万元人民币的USDT,但是报警后,并未处理。实际上,由于虚拟货币的特殊性,再加上央行、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在2021年9月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银发〔2021〕237号)(以下简称为“924通知”)也提到:“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这就导致实践中碰上这种诈骗虚拟币的事件,有些办案机关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所以,有人就趁机钻这个空子,“空手套白狼”,线下诈骗他人虚拟币!
但是,刘律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此类案件中,存在哪些辩点:比如,虚拟币是否有刑法财产属性?犯罪所得又该怎样认定?
二、虚拟币是否具有刑法中的“财产”属性?
(一)从法益来看,诈骗虚拟币的行为,并没有侵害公私财物所有权。
首先,像本文讨论的此类诈骗案,犯罪分子行为指向的标的是虚拟币。然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这就意味着,诈骗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必须是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财物,包括但不限于货币、有价证券、财物性权利等。刘律认为:在案件中,如果行为人骗取了虚拟币,且并未将其变现。那么,由于虚拟币并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属性,比起公私财物,行为人侵犯的法益可能更接近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安全,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当下尚不明朗,其背后是否存在真实价值亦不清晰,无法将其归纳为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更不符合诈骗罪所保护的财产法益。首先,从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现行政策看,无论是央行联合其他部门在2013年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还是在2017年9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以及上文所提及的“924通知”,这些文件均明确规定虚拟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有法偿性,不是真正的货币,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明确禁止并严厉打击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虽然个人可以合法持有虚拟货币,在境外特定的平台支付一定的对价获取、交易、投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但其初始相应的表现形式依然并不属于资金,其本身并无任何实际价值,其市场价格的涨跌来自大众“共识”和庄家的“操盘”炒作,不能因为其价格原因而改变其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本质属性,亦不能因此而赋予其具备财产属性。
第二,从刑法法理角度看,如果强行将虚拟货币等同于法币或者其他财物纳入刑法范畴中的“财物”,可能属于不当扩大解释。由于虚拟货币本质属于数据,不具备财产属性,如果认定其属于财物,就可能超出刑法解释公私财物的限度,同时也超出普通民众的一般预测可能性。
第三,从罪刑法定角度看,我国《刑法》第266条明确规定的诈骗罪的犯罪对象为公私财物,而非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所以,如果认定此种案件的行为人构成诈骗罪,可能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关于虚拟币的刑法财产属性问题,可以参考盗窃虚拟币类型案件。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及裁判倾向看,目前各法院对虚拟货币是否具有财产属性司法裁判不一,并没有对此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并且在学术理论上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民法典》虽然对虚拟财产进行了规定,但关于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理论争议依然存在。实质上,虚拟财产的民法规定只具有宣示性意义,即,立法主体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虚拟财产的属性定位问题,依然需要司法主体根据实践需求进行具体认定。
比如说,在【(2023)沪0120刑初27号】安某非法获取他人虚拟币案件中,被告人安某将他人的钱包币转移到了其掌控的两个账户,然后在火币交易所将涉案的USDT、BTC等虚拟币变现为人民币,共非法获利人民币38万余元。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安某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从该判例可以看出,司法机关更倾向将被盗的虚拟货币的本质属性认定为数据,而非财物。
所以,虚拟货币并非刑法意义上的财物,不具有盗窃罪构成要件中财物的属性,其本质上是一种电磁记录,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刑法中财产的范畴,如果将网络虚拟财产解释为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属于不当扩大解释,严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一般来说,即使认定盗窃虚拟币的人构成犯罪,那么也是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科处刑罚,而非盗窃罪。
我们认为:关于虚拟币在刑法上的财产属性问题,可以参考对“盗窃虚拟币构成盗窃罪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辨析。因为,盗窃罪和诈骗罪所侵害的法益,都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目前,在盗窃虚拟币的案件中,已有主流观点认为被盗窃的虚拟货币本质属性为数据,非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在当下司法实务中,对于盗窃虚拟币的嫌疑人,法院大多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处理,而不是盗窃罪。
那么,如果是像本文讨论的诈骗虚拟币案件呢?其一,虚拟货币属于数据而非财物,那就不能定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了对吧?其二,我们《刑法》中,又从未规定过“诈骗虚拟币罪”或者“诈骗数据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可不能随意创设一个罪名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其三,诈骗行为是否能等同于非法获取行为,即,诈骗虚拟币能否像盗窃虚拟币一样,定一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其四,如果认为上面的罪名都不适合评价诈骗虚拟币的行为,那总不能不去定罪吧?这里面的问题都很值得深入探讨。
(三)不宜以虚拟币折算的人民币来认定案件的犯罪所得。
由于本文所讨论案件的涉案标的为虚拟货币,依据“924通知”第2条可知:“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所以,无论是司法鉴定机关,还是公检法部门,都不宜违反国家监管政策,直接对虚拟货币进行定价。故而,对此类案件涉案资金的金额认定,如果办案机关参照的是将虚拟币折算的人民币金额,事实上已经属于是为虚拟币定价的工作,并不妥当。
三、在案证据需要形成完整证据链,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一)怎样的在案证据,才能认为具备完整证据链?
首先,犯罪嫌疑人在主观上,应对自己的诈骗行为具备“明知”。如果嫌疑人的角色更多是作为资金提供方,并不干涉或深入了解资金的具体用途和流向,那么可能就难以在主观上认定其“明知”他人将资金用于诈骗目的,亦难以支持其和他人具有共同诈骗的主观故意。
其次,从客观上看,诈骗罪侵犯的是财产权益,涉案金额直接反映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对于涉案金额的认定必须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以确保裁判的公正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完整的证据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根据《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因此,在客观上,如果想要认定犯罪嫌疑人确实参与并实施了被指控的诈骗行为,其一需要有相关交易的转币流水记录,其二则需要犯罪嫌疑人自认或同案犯供述的与转币流水记录相对应的钱包地址。只有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交易涉及的虚拟币收款钱包地址经犯罪嫌疑人或其同案犯承认属于犯罪嫌疑人本人的基础上,才能认为其可能实际参与了相关交易,从而形成完整证据链,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二)从区块链浏览器查询的境外数据,能否作为定罪的客观证据使用?
我们在前文“三、(1)”中提到,完整证据链需要具备相关转币记录。那么,如果该转币记录是办案机关通过某未经国家信用背书的区块链浏览器查询到的结果,其所载数据能否作为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的刑事诉讼证据来使用呢?
首先,从浏览器的发行主体来看,目前,某主流的区块链浏览器的发行主体是一家早已退出中国市场的境外私人公司,如果办案机关用该公司的“产品”作为我国刑事案件中的证据,那么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值得商榷。早在2021年10月13日,该公司就发布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监管政策的通知》,表示自2017年9月开始就把业务重心转到国际市场,不针对中国大陆市场进行推广和服务,也下架了所有的中国大陆地区的应用市场软件。那么,试问:用一个业务范围现在根本就不在中国的公司推出的产品,来查询出的记录,怎么能够作为发生在中国的刑事案件的定案证据呢?如果办案机关认为能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又要如何去界定其中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和本案件的关联性呢?
其次,虚拟币交易记录在证据种类上应当属于电子数据。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是指被用以证明嫌疑人有罪的电子数据是否完整、真实、未经篡改且能还原案件真相,具体而言包括三方面要求:一是电子数据载体的真实性,即承载电子数据的原始介质是否进行妥善保管和安全移送;二是电子数据来源的原始性、真实性,即电子数据在取证过程中未被污染或篡改,系原始数据;三是,电子数据内容的同一性,作为鉴材的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算法要保持一致,保证电子数据在移送过程中、保管过程中、诉讼过程中未被删减、增加或修改,且收集的电子数据与案件内容关联,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结合两高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十七条的规定:
“当事人对区块链技术存储的电子数据上链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有合理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下列因素作出判断……”。
虽然该规则针对的是在线诉讼活动,但是,其中对于区块链电子数据是否具备法律上的“真实性”,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判断标准:“(一)存证平台是否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提供区块链存证服务的相关规定……(三)存证平台的信息系统是否符合清洁性、安全性、可靠性、可用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也就是说,将区块链浏览器上查询到的数据作为证据使用的前提:一是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二是保证存证平台的合法合规。但是,境外平台的区块链浏览器的资质不明,显然达不到该标准。
最后,办案机关如果使用的是一家在境外的私人公司,那么其发行的浏览器所提供的境外电子证据,在收集和使用过程中更需谨慎。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第5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境外收集的证据,应当审查证据来源是否合法、手续是否齐备以及证据的移交、保管、转换等程序是否连续、规范。”
《刑诉法解释》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对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对材料来源、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提取人、提取时间等进行审查。经审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提供人或者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对材料的使用范围有明确限制的除外;材料来源不明或者其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综上所述,办案机关应当谨慎对待区块链浏览器提供的数据,不应轻易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是对法律严谨性的尊重,也是对司法公正性的维护。毕竟,任何被为刑事案件证据的电子数据,都需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都能够真实、合法地反映案件事实。
四、律师有话说
在虚拟货币交易的法律领域,特别是在涉及诈骗虚拟币的案件中,如何定罪和量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碰上虚拟货币诈骗,别慌,对于此类争议或案件,寻求专业法律意见至关重要。刘律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建议尽早咨询专业人士,早点化解法律风险。
生活中的难题,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解决,看完本文,相信你对 有了一定的了解,也知道它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你还想了解上海市诈骗罪量刑标准2020年的其他信息,可以点击酷斯法其他栏目。

 家庭婚姻
家庭婚姻 刑事辩护
刑事辩护 债权债务
债权债务 公司法
公司法 房产纠纷
房产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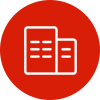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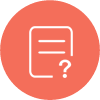 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 医疗纠纷
医疗纠纷